那个白杨簌簌的午后,我想起了曹阳老师
- 外汇
- 10小时之前
0 - 4
(来源:上观新闻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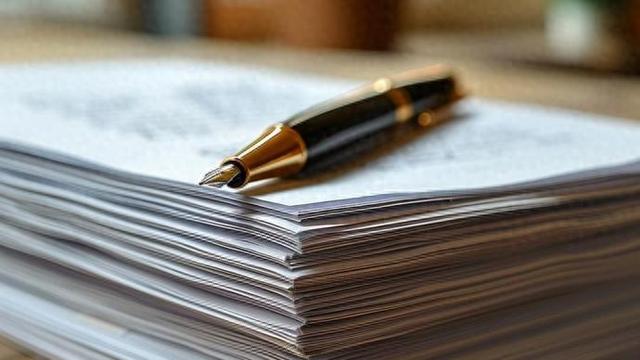

那个午后,我到航头镇的傅雷图书馆还书,顺道走进了镇上的一座杨树园。满园白杨叶在风中簌簌作响,恰似“白杨多悲风,萧萧愁煞人”的意境,曹阳老师的身影,便这般在叶声里清晰起来。
2024年11月24日,91岁的曹阳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曹老师曾任《萌芽》主编。众多文学青年,因为《萌芽》,因为曹老师,缩短了从此岸到彼岸的时光;对他们而言,《萌芽》和曹老师有“推窗望月”之功。
作家李伦新年轻时,在当时还在《青年报》工作的曹老师执编的副刊上发表了几篇诗歌习作之后,创作热情高涨,开始写小说。他将小说《离别》寄曹老师后,却迟迟未见刊发。终于,小说见报了,李伦新非常兴奋,可细读一遍,感觉字句间似有不同。因没留底稿,他一时无从比对。不久,收到曹老师来信,展开信纸,他大吃一惊!虽然是他《离别》的手写原稿,但已被剪剪贴贴、勾勾划划,做了许多修改。作为编辑的曹老师在附信中叮嘱他,要仔细对照修改后的段落、句子,乃至文字和标点符号,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改和该怎样改更好。
看着面目全非的小说稿,想着曹老师为自己的小说耗费的心血,李伦新感慨万千!
后来,李伦新又在《青年报》副刊发表了小说一篇,占了整整一版,还配了三幅插图,收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。除去请同事,他还用这笔钱去济南路旧家具市场买了一张老式写字台。李伦新说,每当看到这张“写来的写字台”,就会想到被曹老师剪剪贴贴、勾勾划划,作了重大修改的小说。

曹老师于我,亦是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。在我的文学旅程中,是他陪我走过一程山水,又护我一路繁花。
1990年,一场文学讲座上,我认识了时任《萌芽》主编的曹老师。1992年,《萌芽》刊发了我写象棋棋手生活的短篇小说《独坐黄昏》;1995年,《萌芽》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《汉白玉》与中篇小说《黑黑白白》。三篇作品的问世,如三簇火种,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。为进一步支持我的创作,曹老师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评论文章《看似平淡却深邃》,对我的小说予以肯定与点拨。
曹老师退休后,我常去他府上探望。有一次,他对我说,人到中年,生活阅历已然丰厚,不妨静下心来,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。
2010年,我的长篇小说《褐色木门》完成。2011年,这部作品获得了《小说选刊》年度长篇小说征文二等奖。曹老师由衷地为我高兴,欣然应允为小说作序。不仅如此,他在审读时,还逐字逐句校正了小说中的不当之处与欠准之词,字里行间满是细致。
2014年,我也退休了,去曹老师家的次数变得频繁。我去曹老师家,多半是下午两点左右,他午睡以后。每一次去,都是在他的书房里,一聊,就是两小时。
曹老师曾跟我说起,他刚任《萌芽》主编时,编稿之余,创作的激情在心底一次次翻涌,可终究分身乏术,只能一次次与灵感擦肩而过。言语间,他难掩遗憾之情。
20世纪50年代初,曹老师到冀中平原实地采访,依据真实人物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平原歼敌记》。1958年,《平原歼敌记》即将出版时,他被错打成“右派”。1960年,《平原歼敌记》终于出版,署名却换成了当年的采访对象。不少人认为曹老师应该索回应得的稿费,曹老师却淡然道:“《平原歼敌记》易名出版,是因为历史的原因。只要再版时恢复我的名字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后来,出版社再版此书,补上了曹阳的名字。
曹阳是苏州市同里镇人,其曾祖父官至“同里同知衖门”。在曹老师家中聊天时,“苏州同里”这四个字,经常出现在他的话语中。感受到曹老师的思乡之情,我特意为曹老师刻了两方印章,一方“家居江南”,一方“梦在姑苏”。
曹老师曾应邀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落笔:“世界老了,文学之树常青;爱情老了,写爱情的作品常新;人老了,爱文学的心永远年轻!”
默念着曹老师的这番感怀,我告别了“白杨悲风”,抬眼望去,天是那么蓝,云是那么白……
原标题:《那个白杨簌簌的午后,我想起了曹阳老师》
栏目主编:黄玮 文字编辑:黄玮 题图来源:上观题图
来源:作者:丁旭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