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探周易 殊为不易
- 外汇
- 2小时之前
0 - 2
▌陈鸿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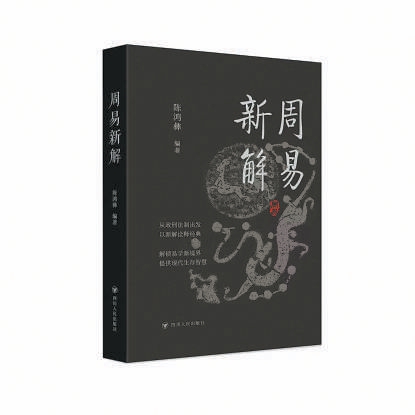
《周易新解》陈鸿彝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
《周易》是什么?在我看来,它是中华现存的第一部哲理之书:第一部原创之政法经典,是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、社会管理之经验总结,也是清明法治、趋吉避凶的智慧结晶。我在这本《周易新解》里做了义理性的新探索,尝试拓宽易学的视野。
易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分阴阳、互渗透而对应的。所谓对应,既揭示了事物之间相应的对比、对称、对等、对齐,也包括对立、对抗。它更强调事物之间的共生共存、和谐共进,即总体平衡反对一家独盛;因而更适应系统论、结构论的理论诉求,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学说的哲理需要,为人类的协同发展、安全互助提供了无限多样的方案选择。《周易》中居安思危、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,趋吉避凶、预防为主的安全策略,慎狱恤刑、不侮鳏寡的刑狱理念;兼容并蓄、求变求新的革新思想,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担当精神,天人合一、生生不息的哲学原理,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。我在《周易新解》中对此做了明晰的阐释。
我认为,人的价值在《周易》中被提升到与天地齐平的高度,肯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“崇高莫大乎富贵”:这是“人”的觉醒。它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神圣观:“利用出入,民咸用之谓之神”,“备物致用,立成器以为天下利,莫大乎圣人”,“以美利利天下,不言所利”。故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这些远古圣人都是终生劳动者,受到广泛的尊重。谁都不是出身高贵者,不是天生的圣人;他们是实干家,事业有成之后,才被民众推尊为圣人的。故而本书认为,古来的圣贤崇拜,就是对劳动、创造力的崇拜。对于这种创造精神,相传孔子所撰的《系辞传》中有云: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:以言者尚其辞,以动者尚其变,以制器者尚其象,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“往来不穷谓之通,见乃谓之象,形乃谓之器,制而用之谓之法;利用出入、民咸用之谓之神。”遗憾的是,后世并未将这一点发扬光大,反而流向了空洞化、玄虚化。
在我看来,《周易》的六十四卦中也体现了礼、法、禁、令与罪、刑、狱、讼等法学概念,这同样是对人的尊重。它不语怪力乱神,把社会灾凶视为政局清明的指标,要求以良政善法为社会做安全保障:它指导在位掌权者担当起解除民生疾苦的责任,希望他们能“理财正辞、禁民为非”,“利用正法”来形塑人、形塑良性社会。这里有裒多益寡、称物平施的施政方针,有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的人性规范。事实上,先秦百家对刑狱的论述中《周易》是最早的。老庄没有提到过罪、刑的相应概念,墨子没有讨论过罪与刑的立法司法问题;后起的法家,倒是详明地阐述了自家的刑狱主张,但其中心思想是“唯法为治”论——它把法律裁决、军事裁决推向了极端。
狱政是是非善恶的社会聚焦,为万众所瞩目。政清法明刑简,历来被认为是从政者的底线。比如《贲卦·象》说“君子以明庶政,无敢折狱”;《丰卦·象》说:“君子以折狱致刑”;《中孚·象》说“君子以议狱缓死”……这里一再讲的就是明慎用刑、议狱缓死之狱政原则。《周易》的明罚敕法、慎狱恤刑、不侮鳏寡等一系列人性主张,明确了清明政治的价值取向,打造了法治话语表达的最初范式。比如《周易》第四卦“蒙卦”倡言“利用刑人,以正法也”。清人黄宗炎对“利用刑人”的解释是:“刑土而陶,刑金而铸,必先正其模范,而后求肖焉。刑人亦犹是也,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。”可知“刑”的第一要义是“形塑”而不是刑杀,即规范人、塑造人。那么,要想形塑公民、形塑优质社会,其先决条件就是主事者先正其身,正身而后正法,正法而后正人。
《周易》书中认为,国家祸患之有无,责任不在庶民,而在“君子”,“正法”的社会责任在“君子”身上。“议狱缓死”,要求充分讨论狱情,不轻率判人死罪;“折狱致刑”,是说要析案折狱而后再定罪量刑,审理清楚而后才依法惩罚,不擅断、不刑人立威。“以明庶政”“以明罚敕法”的要求,为清明法治设置了理想路标。《旅卦·象》说:“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”。这“不留狱”,正是对人的自由生存权的尊重。《豫卦·象》说“圣人以顺动,则刑罚清而民服”——任何法律,一离开民众的真心支持,不能契合人心,不能获得民众的实践支撑,必然失败。它的提出,标志着先民早已走出了同态复仇、等价复仇、血亲复仇的蒙昧。这些话语,在今天看来仍旧值得深思。
